编者按:美国学者赫伯·林撰文指出,美国防部内部对“信息战”、“信息作战”、“心理作战”和“影响力作战”的理解参差不齐、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反映出国防部在“信息作战”和“心理作战”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紊乱。虽然,网络司令部尝试利用网络行动制造心理效果值得称赞,但国防部未能从整体上纳入信息作战的心理因素,并将其整合到网络空间作战。国防部需要继续努力,将心理作战(更大角度上的信息作战)完全纳入军事行动。文章全文翻译如下,供读者参考。
今年年初,Lawfare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将“网络作战”当作是“心理作战”,这一点令人质疑。无论是“网络作战”还是“心理作战”,都是美国网络司令部常见的战役活动。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源自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在NPR上看到的,另一篇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的。前者讨论了美国网络司令部过去的活动,后者讨论了未来可能进行的活动。总之,这两篇文章都使用诸如“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信息作战”(information operations)、“心理作战”(psychological operations)和“影响力作战”(influence operations)之类的术语来描述这些活动。
看完此文,我确定国防部政策对于这些活动概念从条例和概念理解上都产生了混淆。这篇文章印证了这一点。
下面就回顾一下国防部有关“信息战”及相关术语的演变情况。通过回顾发现,即使在国防部内部,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也是参差不齐、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并且经常交叉使用,即使所描述的是性质不同的活动。
直到2018年,美国联合军事条令才确定,只有六种联合功能是在各级战争行动中都能见到的,即:指挥与控制、情报、火力、行动与机动、保护和保障。2018年10月,美军发布《联合作战条令JP 3-0》,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18年的联合条令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功能。重要的是,这七个功能(包括信息功能)被描述为所有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信息功能包括三组活动:一是了解作战环境中的信息;二是利用信息影响相关行为者的行为;三是支持友好的人为和自动决策。
国防部在《JP 3-13联合信息作战条令(1998)》中将“信息战”定义为“在危机或冲突(包括战争)期间进行的信息作战,以实现或促进特定对手或多个对手的特定目标。”当时,国防部将“信息行动”定义为“在捍卫自己的信息和信息系统的同时影响对手信息和信息系统的行动。”有趣的是,这个定义与美国国防部今天所理解的“网络空间作战”非常相似。
2006年,美国国防部放弃了“信息战”一词,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作战”。该部门在《JP 3-13 信息作战(2006)》中定义的“信息作战”,除了计算机网络作战外,还包括电子战、心理战、军事欺骗和作战安全。《JP 3-13(2006)》还引入了“信息环境”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收集、处理、传播信息或对信息采取行动的个人、组织和系统的集合”,并指出“信息环境”是人类和自动化系统观察、定位、决策并根据信息采取行动的场所,因此是决策的重要环境。”
国防部在《JP3-13 信息作战(2012)》中给“信息作战”重新下了定义。新定义强调了信息环境的重要性,并将信息行动的既定重点从“行动清单”转变为更广泛定义的组织活动。“信息作战”成为“在军事行动期间,与信息有关的能力与其他行动方式协同作用的综合部署,在保护自身的同时,影响、破坏、改变或篡夺对手和潜在对手的决策。”通过删除原先定义的信息作战活动清单,《JP 3-13(2012)》进一步强调,信息作战活动应注重使用与信息相关的功能,产生理想的“信息”效果。
国防部门并没有给 “影响力作战”一词下过正式定义。但根据兰德公司在200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影响力作战”被定义为“利用国家外交、信息、军事、经济和其他能力,在和平时期、发生危机、爆发冲突及冲突后,以培养外国目标受众的态度、行为或决定,从而进一步促进美国的利益和目标。” 尽管兰德的观点没有权威性,但兰德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数十年来一直是国防部的一支重要分析力量。
在美军的《JP 3-13.2 心理作战(2010)》及其后续《军事信息支援行动》(结合2011年12月20日的变更1)中,国防部将心理作战(PSYOP)或军事信息支持作战(MISO)定义为“向外国听众传递选定的信息和指向,以影响其情绪、动机、客观推理,最终影响外国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行为,以这种方式帮助发起者达成预期目标。”其他军事行动,例如动能打击,也可能会产生心理影响,但不被视为“心理作战”,因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影响物理环境中的某些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心理作战”的定义不包括反宣传活动,也没有明确承认美国观众可能成为对手“心理作战”目标的可能性。
国防部在《JP 3-12(R)网络空间作战(2013)》中首先引入了“网络空间作战”一词,后在《JP 3-12(2018)》中修改了定义。两种版本都将网络空间能力定义为“一种在网络空间或通过网络空间产生效果的设备、计算机程序或技术,包括软件、固件或硬件的任何组合”,将网络空间作战定义为“以通过或利用网络空间达成目的为主要目标的网络空间能力。”所有网络空间作战不外乎是以下三种网络空间任务:一是国防部信息网络作战;二是防御性网络空间作战;三是进攻性网络空间作战。《JP 3-12(2018)》指出,网络空间就是一种介质,通过它可以部署信息相关能力。
以上回顾了美军联合军事条例有关网络作战等活动的定义演变情况,而这些条例被广泛认为是了解各种美军思想术语含义及其应用的最权威资料。由此可见,即使在国防部内部,不同时期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也含混不清且相互缠绕。因此,美国公众,甚至是国防部自己,经常乱用“信息战”“信息作战”“心理作战”“影响力作战”以及可能的“网络空间作战”术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它们并不是同义词。
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信息战”“信息作战”“心理作战”和“影响力作战”等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混淆?
我质疑国防部的文化体系(又称权势等级),他们认为动能军事专业(例如装甲、步兵、水面作战)比非动能专业更值得尊重。试想一下,2018年以前,在制定联合条令时,并没有把信息功能与其他联合功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就在那年,美国国防部引入了信息功能这一概念)。因此,人们对非动能作战缺乏敬意并对这类问题重视不足,我并不感到惊讶。每个人都很忙,让他们去熟悉那些他们认为并不太重要的事情很可能是没有积极性的。
公众的敏感性在混淆定义本质的过程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例如,2011年,“心理作战”一词被“军事信息支持作战”取代,根据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指示,“心理作战”被解释为“通常是指宣传、洗脑、操纵和欺骗。”
国防条例所构建的这些概念的历史和演进已发生改变。而国防部中不从事网络或军事信息支持作战的人员,经常把“信息战”和“信息作战”等术语和概念理解成为社会讨论中使用的含义,而不是像国防部网络和军事信息支持作战专家们所理解的那样。
这些概念理解上的不一致最终引起了概念的混淆,进而可能导致资源和能力方面的误配和错位。例如,由于不了解不同任务的含义和所需技能,这种混乱可能使国防部更难招募、雇用和培训合适的人担任网络和军事信息支持作战职位。如果不能明确任务完成绩效的评判标准,则绩效评估也将更加困难。
以上讨论还反映出,国防部在信息作战(相对动能作战而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紊乱。对于心理作战,情况更是如此。网络司令部尝试利用网络行动制造心理效果值得称赞,实际上至少部分心理作战专业人士已进驻网络司令部。不过,我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即国防部网络战社群的强烈技术重视,以及更广泛的国防部关于心理战的观点,并未能使国防部从整体上纳入信息作战的心理因素并将其整合到网络空间作战。我所关注的是,国防部需要继续努力,将心理作战(和信息作战,从更广的角度看)完全纳入军事行动。条例中的混乱反映出国防部需要这样的努力。
本文是一篇同名文章的摘要,同名文章将在2020年夏季《网络防御评论》(CDR)专刊上发表。
赫伯·林(Herb Lin)博士: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网络政策与安全高级研究学者,胡佛研究所网络政策与安全汉克·霍兰德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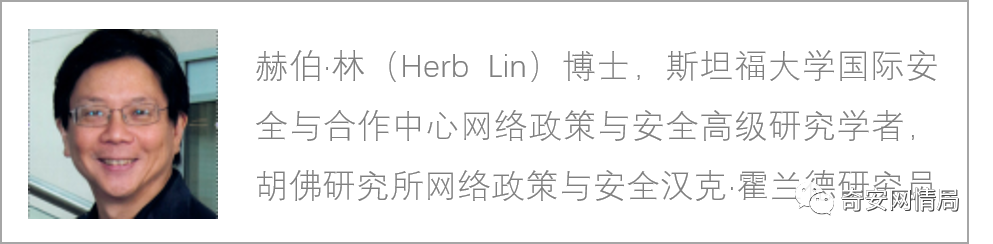
声明:本文来自奇安网情局,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