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王浩/编译
自: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2023年7月

【知远导读】本文是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研究员杰克·沃特林撰写的研究报告,着重阐述未来战场上地面部队指挥控制体系结构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未来战场的发展趋势,并指出这些发展动态是推动地面部队指挥控制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对未来地面部队指挥控制体系结构的设想,包括应用于战术编队的移动自组网、应用于火控系统的异构杀伤网、应用于部队指挥的战斗云。作者对未来战场及其对指挥控制的要求进行了深入而客观的分析,提出的设想具有独到见解,对相关研究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报告全文约2.9万字,篇幅所限,推送部分为节选。
推动陆战发展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武器、后勤、社会能力、通信。武器的发展同时推动运用武器效果和抵消武器效果的战术发展变化。例如,随着火药的出现,逐步将保证生存能力的手段从占领高地转变为依靠分散和挖掘战壕。1新型后勤能力的发展决定能够保障的部队规模、投送部队的距离和部队运动的速度。所以说,内燃机极大加快了作战节奏。2社会结构决定可以从事的战争规模,进而决定战争性质。如果一个社会只有能力生成作战部队,那么它可以控制的范围有限,这就造成利用暴力作为影响力工具来驱动冲突动态,使劫掠成为主要功能。相比之下,一个有能力征召数百万部队的工业化社会可以切实地结束冲突。同时,通信提高灵活性和复杂性,军队能够加以利用。例如,我们很难想象战区之间不能互相通信的话,又怎能做到同步。3
现在很流行的说法是技术进步推动“军事革命”,4但是必须指出,新兴技术往往需要30年才能充分成熟,达到真正引入军队,进而极大改变战争性质的程度,例如,到索姆河战役的时候,机枪已经服役了30年之久。发展的速度有时也会加快,尤其是当两个以上因素的发展互相配合的时候。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军事活动的进步是技术突破推动的,更贴近真实的看法是,随着某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能力本身成熟到足以普遍采用,军队做出调整适应。真正改变战场的部队往往不是第一个运用某种能力的部队,而是第一个掌握如何大规模运用的部队。5

随着战场超级互联的出现,可以认为我们即将到达原定的30年前瞻,届时互联网和个人移动通信的作用已足够成熟,可以推动战争性质发生变化。这时就像以前的技术发展一样,这并不是说数据在最近的战场上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地面部队对数据的使用基本上是重复当初在模拟时代设计的结构,要么就是表现老式战斗序列所带有的特殊内容。军队或许已用软件定义电台替换了模拟技术,但是看看现代军事指挥部的布局、人员和功能,还是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样子。随着不断增加的新型系统和能力,军队不断膨胀,但是根本结构和逻辑仍旧一样。
军队原封不动与超级互联对某些民间组织造成的变革性影响形成鲜明对比。在数据访问全面普及的影响下,产生大量关于未来战争的军事理论研究,但是战场发电的实用性、特征管理和通信保密都对许多民用方法的采用造成限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部队的结构和装备只有更好地、高效安全地使用新技术,才能取得相对于敌手的优势。例如,法国发明无烟火药后,有意掌握这种先发优势,结果却制造出列强当中最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小武器,这导致法国的领先十分短暂。6所以说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对。
目前关于数据和现代战场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网络体系结构的高技术研究,通常具体研究加密方法和承载类型等新技术,围绕在案项目进行。第二类是基于多域集成7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8等军事概念,通常描述完美态势感知的最终状态,基本不涉及技术在实践中的不足。前者扎根于现实,但是无法研究部队如何随着通信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作战方法。它着眼于完善现有能力或加速推进现有流程。而后者的前提条件是技术将会跟上概念的进步。
本文试图沟通这两种文献之间的鸿沟,因而介绍技术发展情况,并研究技术发展如何推动地面部队编制结构和指挥控制(C2)方法的变化。本文创建一个概念框架,用于思考现代通信给地面部队带来的机会,部队在编制上怎样才能抓住这种机会,以及需要怎样的通信体系结构才能支持这种编制结构。本文并不研究现有的以军事通信现代化为目标的项目。我们要了解“墨菲斯”(Morpheus)、“水星”(Mercury)、“黄道十二宫”(Zodiac)、“忒亚”(Theia)等项目的进展情况,但是过分重视这些项目有可能使这些需求变得具有决定性作用。当然也不应该把本文视为系统体系结构方面的研究,而是应当将它视为一项描述陆地域指挥控制整体运行体系结构的工作,目的是更好地在数据丰富的战场上把握机会,降低新出现的风险。
现代通信体系结构着眼于将联合部队连接起来,极大依赖太空域和网络域,所以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以地面部队为重点。首先,地面部队在管理庞大数据方面存在着一些完全不同的挑战。产生庞大数据量的原因主要是地面部队中需要连接的点数量特别多,而与更集中于平台的域相比,单兵系统可用电量较少,同时复杂地形还会造成干扰。9通信体系结构的变化还对地面部队指挥控制产生这个域特有的影响。所以不能说本文排斥其他域。本文探讨的网络有的或明或暗具有联合性质,但是在谈到对部队作战造成的影响时,这里只阐述涉及地面部队的内容。
可能有人会说本文并不是主要阐述指挥控制问题,而是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C4)问题。这样说是对的,但是C4这个缩略语根本没什么用处。指挥控制之间有关系,但其实是不同的职能。前者涉及设想目标,然后向部队下达这个目标;而后者涉及指导执行计划来实现规定目标。相比之下,通信和计算机不属于职能,而属于工具。所以说,本文说明通信和计算工具的发展在现实中怎样与指挥控制的实施发生相互作用,并改变后者。
还应注意区别通信和计算机。许多通信设备其实就是计算机,所以这个缩略语并不是很好用。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理解成承载/网络与服务/应用之间的区别,就容易看清了。前者说明如何传送数据,而后者涉及在设备上对数据做了什么。拿手机这个日常工具举例就更有利于理解。手机可以使用3G、4G、5G或WiFi网络,这些是不同的承载。然而,所传输信息的加密、解密、呈现和输入可以通过许多种服务进行管理,比如有WhatsApp和Signal等不同的应用程序。
本文主体分为三章。第二章概述现代通信带来的机会和风险,以及如果能够实现机会或降低风险,会促使部队怎样对现有指挥控制实践进行调整。第三章以第二章所述驱动因素为依据,分析必须采用怎样的体系结构才能投用所述能力。第四章说明要想有效运用第三章所述系统,部队必须适应哪些非结构性影响。本文采用多种方法,但是核心内容的依据是对新型通信系统进行贴近现实的实验,以及研究那些检验和运用各种通信系统的演习和行动。

变革的驱动因素
为了认识到怎样调整地面部队指挥控制的实施,才能更好地运用新型能力或降低对传统结构部队带来的风险,必须理解这些能力对现有指挥控制体系结构造成怎样的压力。本章概括了我们评估认为的几种会成为变革驱动因素的机会和风险。
态势感知成为战斗倍增器
随着计算机微型化,当今战场充满了各种高逼真度的传感器和探测器,能够长时间保留并进行传输。随着数字化系统扩散,使现代战场成为数据丰富的战场;这就提出能不能访问和利用可用数据的问题。在车辆和人员装备上结合雷达、电光、声学、电磁、热学和位置传感器载荷,起到显著效果,体现在发现敌人的距离大大增加。10如果能够在某个平台上融合多部传感器,并利用边缘处理进行算法询问,这个效果就会成指数放大,同时如果可以共享传感器图像,还能进一步加大。在历史上,以前都是由人实施并记录战场上的目标探测和分类,语音是实时传播消息的唯一手段,而这会限制可以共享的信息数量,还不能迅速更新。现在,一旦人类将观察结果记录为数据,加上通过传感器自动将对象进行分类,在数据适于进行整理的情况下,将会极大增加可以融合的探测结果。
如果可以访问数据,就可以大幅度加强部队人员的态势感知。态势感知的定义是一名军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自己相对于友邻和敌人的位置,自己周围的人都想做什么。在态势感知强于敌人的情况下,就使部队拥有了竞争优势。11举例说明,一支部队中己方每个实体都能准确跟踪自身位置并交流这个信息,即每名军人都能够获知蓝军跟踪信息。如果不能访问蓝军跟踪信息,就会对作战构成许多制约:首先,在时间上会有影响,因为发现目标运动情况后,必须先确认是敌方运动,然后才能发送信息或召唤对敌施加打击;12其次,必须消除射界与进攻轴线之间的冲突,这将对机动造成限制。这就要求在单位之间划分界线,而这将在队形中间造成可被敌利用的间隙(因而也是薄弱点);最后,会对军人心理造成影响,因为当支援部队或友邻部队都在视线之外时,军人不确定自己会遭到怎样的攻击,或者会得到多大的支援。而共享蓝军跟踪信息可以做到:使军人更快打击敌人,同时降低蓝军彼此误伤的风险;对部队划定动态分界线,进而提高机动自由;让军人知道自己会得到支援,进而获得心理安慰。
我们将态势感知称为战斗倍增器的理由是它给任务式指挥带来变革性的影响。原来认为任务式指挥的前提条件是军人要发挥主动精神,在没有集中指示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位置,使它符合总体意图。13当然,当多位指挥官在所掌握信息有限的条件下发挥判断力,得到矛盾或冲突的结论时,就会出现风险。全体部队掌握的态势感知越强,可以依赖的背景信息就越多,就可以自信地实施任务式指挥。14可以将之称为“汇聚”。如果军人能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轨迹,如果可以在这个条件下实施任务式指挥,军人就可以利用态势感知进行汇聚,动态填补缺口和利用机会,而这可能大大偏离最初计划,却不会造成部队混乱。简而言之,通过态势感知实现边运动边改变轨迹。在为汇聚创造条件后,还可以减少司令部的必要干扰,使指挥官可以提前思考,而不是一心只想着将部队的各种行动结合在一起。

为了实现这种态势感知,必须做到让数据在部队里横向移动。例如,军长没必要知道某个步兵班应该从左边还是右边绕过障碍物。但是,如果这个步兵班通过运动进入另一支友军指挥官的视界,这位指挥官就非常需要了解这个班的身份。老式军事通信体系结构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运行。传统上看,军事通信的结构可以让数据在各级别之间上下流动。当然在通信网这种群组中会有通信,但是通常采用轮辐式体系结构,数据在分队之间向上再向下传输,而不是直接在整个编制中流动。在这种系统中,有一位发话者始终列为优先,所以困难就在于不可能像大量纵向数据传送那样在同一个网络上进行大量横向数据传送。
横向数据传送和汇聚还对指挥官提出挑战,因为通过相同数据累积,会细化高级军官的粒度,鼓励他们查看并纠正下属的活动。在下属实施任务式指挥时,当同时上级指挥官能看到他们运动的情况下,风险就在于指挥官会尝试行使控制权,这只会减缓并混淆活动,而不是提高执行的精度。随着态势感知加强,战斗效能将会提高,但是必然会推动建设不同的通信体系结构和新的指挥文化。
饱和
虽然可以通过横向传送相关数据来实现态势感知,但是处于战术边缘的单位处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接敌部队利用所获信息可以产生的效果也同样是有限的。15此外,随着数据不断累积,既可以改善某个级别可以产生的判断和效果,也可以提高处理和使用信息所必需的能力。数据本身并不是力量倍增器,数据只有在与有用户有关时才是力量倍增器。可是要想确定哪些数据与用户相关,还存在许多难点。而且,数据相关性是有保质期的。如果摄取、分析和确定信息相关性的过程比信息对用户有用的时间还长,那么数据就不是倍增器,反而会成为一种浪费能力的负担。从历史上看,划分级别不仅要看控制范围,还要看关注内容的时间跨度。16上级指挥部应该进一步提前思考,而且要具备这种能力。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如果能在正确的地点迅速累积信息,就能汇聚各级的效果,达成决定性优势。例如,当旅级发射导弹时,如果军一级可以对敌保护导弹打击目标的防空系统投送网络载荷,导弹命中目标的机会就会提高,而投送载荷时使用的可能是师级电子战(EW)效应器,发现敌防空系统目标的可能是国家技术手段。相反,火力射程意味着各级通常要同时实施全作战纵深打击。在战场高逼真度传感器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如果部队能够让正确的传感器把正确的信息发给正确的用户,就比那种拥有信息,却不能传输、处理并据以采取行动的部队占有更巨大的优势。这就是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等概念所提出的前景,17但是这种概念通常都没有解决随之带来的饱和风险。

饱和风险有两种:分析饱和和承载网络饱和。要想避免分析饱和,就要求根据对终端用户的相关性来对信息进行排序。例如,计划小组可能要求尽可能多地获得可用信息。考虑到现代战场产生海量数据,也有人坚信这种功能应该提高级别,或通过后取方式提供,这样就可以利用足够的计算基础设施和分析人员,形成储存和查询大量数据的能力。相比之下,战术指挥官没有能力分析大部分战场数据,何况这些数据中还有许多与他们并不相关。即使许多数据点与他们相关,他们也没能力发现。因此,要么必须把数据提到较高级别进行处理、分析和传播,要么必须采取边缘处理,对已知与边缘战术信息相关的数据进行筛选,这样就能排序后传送给终端用户。18答案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决于对给定数据类型的延迟要求。
如果想做到随时组合所有信息,那么承载网络饱和就会无法避免。19战场上数据量的增加快于可以传送数据的承载容量。通过排序可以减少各位置之间必须传送的数据量,从而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延迟也是一种降低承载网络要求的手段。如果不要求进行低延迟传输,就可以让信息经过低效率的路由来填补空闲容量和未充分利用的链接,也可以等到高优先级信息传送完后再进行传输。相反,优先级高的信息可以通过一切可用手段迅速传送,即使这会挤开低优先级信息的传送。20举个例子,将敌空中和导弹威胁的跟踪质量数据与屏护部队的常规情况报告进行比较,显然以前者为优先。当我们描绘现代军队可能的优先排序时,却并不符合战斗序列。所以说,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跳过所有级别,在部队间快速横向移动,也可能指挥官的信息需求恰恰需要违反优先排序。
耗电量也是饱和对系统所面临威胁发挥重要影响的一个方面,进而也能成为系统设计的驱动因素。21军人携带的电量就那么多。数据处理和分析耗电很大,因而必须集中运行。远距离传输大带宽数据同样耗电很大,而且,如果战术梯队想持续掌握态势感知,耗电量就会是恒定的,然而战场时常会要求重要系统具备以低延迟传送信息的能力(这是必要能力),如果中间元件电量耗尽无法发送数据,系统就会崩溃。如果低延迟或高级别关键信息需求通常经由战术单位传送,就有可能耗尽该部队的电量,导致停电,或者极大提高对电池的后勤保障需求。因此,避免达到饱和,成为了设计未来指挥控制体系结构时的关键决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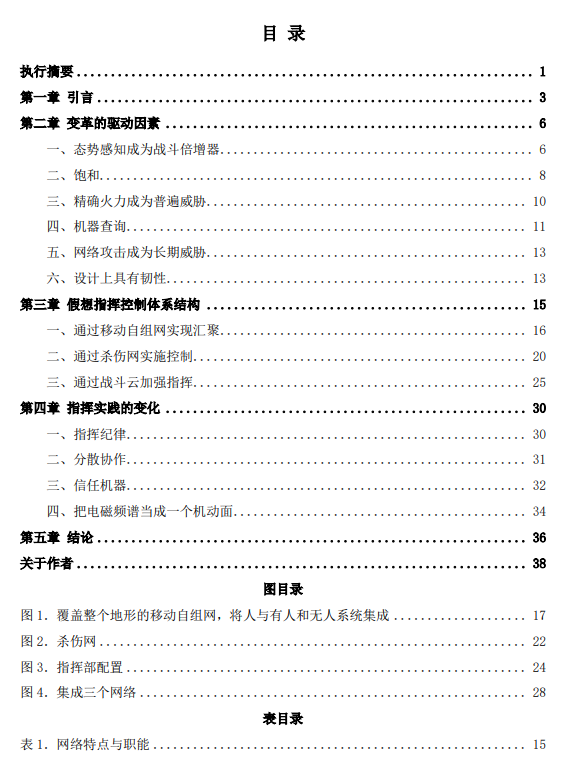
【1】Pushkar Sohoni, ‘From Defended Settlements to Fortified Strongholds: Responses to Gunpowder in the Early Modern Deccan’,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1, 2015), pp. 111–26.
【2】H G W Davie, ‘Logistics of the Combined-Arms Army — Motor Transport’,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31, No. 4, 2018), pp. 474–501.
【3】Brian Hall,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in a Global Conflict: The British Army and Communications Beyond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8, No. 1, 2014), pp. 37–71.
【4】Steven Metz and James Kievit,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Conflict Short of War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1994).
【5】Michael C Horowitz,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Powe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6】Yoel Bergma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Smokeless Military Propellants in France, 1884–1918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2008).
【7】Ministry of Defence, ‘Joint Concept Note 1/20: Multi-Domain Integration’, November 2020,
【8】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 (JADC2)’, last updated 21 January 2022,
【9】Jack Watling, ‘More Sensors Than Sense’, in Justin Bronk and Jack Watling (eds), Necessary Heresies: Challenging the Narratives Distorting Contemporary UK Defence, RUSI Whitehall Paper 99 (Abingdon: Routledge, 2021), pp. 87–98.
【10】Mikael Weissmann and Niklas Nilsson (eds), Advanced Land Warfare: Tactics and Oper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163–68.
【11】Patrick Downes and Michael J Kwinn Jr, ‘Proving Situational Awareness Impact in the Land Warrior Project’, 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Vol. 14, No. 4, 2009), pp. 47–59.
【12】David J Bryant and David G Smith, ‘Impact of Blue Force Tracking on Combat Identification Judgments’, Human Factors (Vol. 55, No. 1, 2013), pp. 75–89.
【13】Uzi Ben-Shalom and Eitan Shamir, ‘Mission Command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ase of the IDF’,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27, No. 2, 2011), pp. 101–17.
【14】Jim Storr, ‘A Command Philosoph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Mission Command’, Defence Studies (Vol. 3, No. 3, 2003), pp. 119–29.
【15】Margaret S MacDonald and Anthony G Oettinger, ‘Information Overload’,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4, No. 3, 2002), p. 44.
【16】Donn A Starry, ‘Extending the Battlefield’, Military Review (Vol. 61, No. 3, 1981), pp. 31–50.
【17】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 (JADC2)’.
【18】David S Alberts and Richard E Hayes, Power to the Edge: Command and Control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ashington, DC: 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 Program, 2003).
【19】Robert Leonhard, The Principles of War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NY: Ballantine, 1998), pp. 16–20.
【20】David Zats et al., ‘DeTail: Reducing the Flow Completion Time Tail in Datacenter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ACM SIGCOMM 2012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s, Technologies, Architectures, and Protocols for Computer Communication, Helsinki, 13–17 August 2012.
【21】John W Lyons, Richard Chait and James J Valdes, ‘Assessing the Army Power and Energy Efforts for the Warfighter’,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arch 2011.
声明:本文来自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