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晓专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 北京 100038; 2.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网络首发《情报杂志》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181220.0856.002.html
摘要
[目的/ 意义]
情报共享与融合是当前执法情报领域的重点、热点与难点问题,美国在推进执法情报共享与融合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做法和经验对推动我国执法情报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方法/ 过程]
通过政策文本与理论文献梳理,运用历史分析与归纳法,揭示自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及其关键成功因素。
[结果/ 结论]
以情报主导警务为指导思想,以共享融合为逻辑主线,以情报分析为核心驱动,通过顶层设计规划推动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与普及,创设灵活的改革调整机制确保随势而变,以隐私权、知情权保障与互利互惠为基石争取广泛信任与支持,培育“信息管家“与“需要分享”的情报文化破除共享壁垒,是美国执法情报改革发展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可供我国借鉴。
关键词 美国 执法情报 情报共享 情报融合 发展轨迹 关键成功因素
引言
美国执法界(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是一个极其分散、复杂的体系,根据 2017 年FBI 犯罪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美国共有 18,547 个城市、大学、郡、州、部落和联邦执法机构[1]。 根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美国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共 15,328 个,全职工作人员 1,050,441 名,其中宣誓警察 701,169 人[2]。
相比我国,美国执法界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分散化,没有统一的中央管理机构与集中管理机制;
二是地方化,绝大多数执法机构与执法力量由地方政府负责运营管理;
三是多样化,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执法机构提供不同的服务,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职责,机构规模从只有一名执法人员到数万执法人员不等[3]。
由于利益壁垒、技术标准、理念观念、组织管理等诸多因素制约,推进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情报共享融合一直是全球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美国这种相对分散的联邦执法体制下问题尤甚。 然而,美国通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在执法情报共享融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近年来我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规划国家安全工作,相继出台反间谍法(2014)、国家安全法(2015)、反恐怖主义法(2015)、网络安全法 (2016)、国家情报法(2017)、核安全法(2018) 等安全相关法律,国家安全制度日益完善,如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推进情报共享融合,以更好地应对“ 国际与国内、网上与网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系统性风险,是新安全时代我国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旨在考察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的发展轨迹与特点,剖析其关键成功因素,为我国提供经验借鉴。
1、“9·11“ 之前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的发展轨迹
1.1、20 世纪 50-60 年代:信息共享从“自发”到“自觉“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美国大多数执法机构未设情报部门,对情报工作的资源投入很少,各部门在信息共享时往往心存疑虑,小心谨慎地护着所拥有的信息,其他有共享意愿的机构因为没有集中的信息交换中心而受到限制[4-5]。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部分执法机构开始自发协作推动信息交换。
1956 年 3 月,来自 7 个州的 26 个执法机构在加尼福尼亚成立美国最早的执法情报协会[6]“执法情报联盟 ”(Law Enforcemen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LEIU),旨在搜集、记录和交换通过常规渠道无法获得的有关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机密信息[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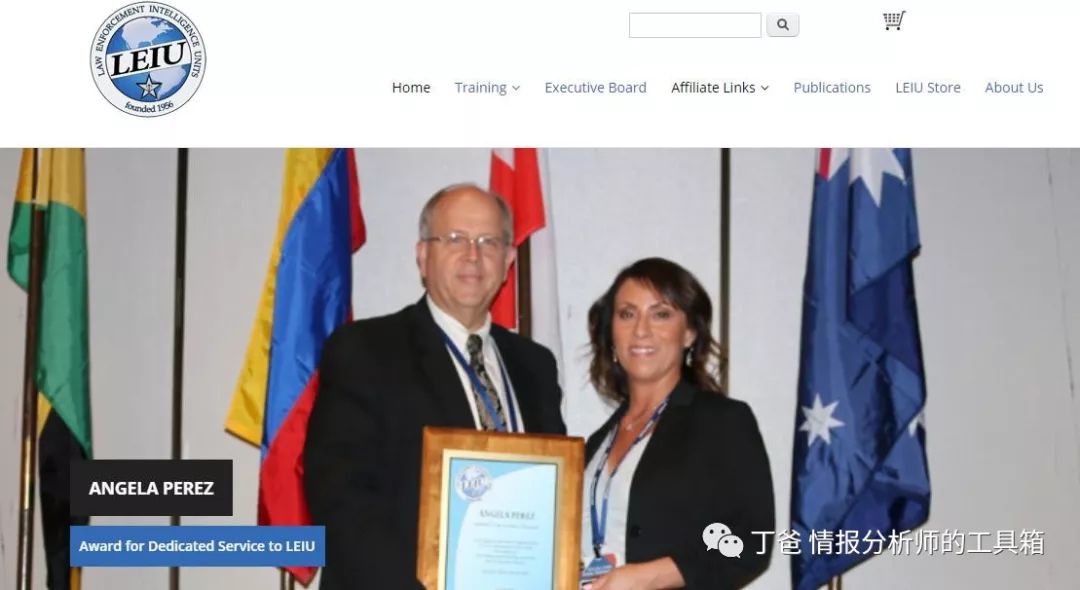
LEIU 作为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之间的涉密信息“交换所“[8],是美国执法情报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范围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目前已有 250 多个成员单位[9],遍及美国,还有部分成员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执法情报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 世纪 50 年代,除了LEIU 外,很少有其他正式的途径进行情报信息交换[5]。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反越战和平运动、校园民主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环保运动等迭起,社会矛盾突显,犯罪高发,联邦委员会和联邦机构开始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地方和州执法机构发展情报能力。
1967 年,美国执法与司法管理总统委员会呼吁各大城市的警察部门都应设立情报部门,深挖有组织犯罪活动,并建议司法部加大财政投入,开发高效的区域情报搜集和分发系统[10]。 同年,FBI 建立“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
1968 年,暴乱原因与预防国家委员会指出,许多警察部门一个主要弱点是缺乏可靠的情报系统,严重制约了警察和政府官员预测、预防动乱以及减少和控制骚乱的能力,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无法获取社区群体及其领袖的可靠信息,无法了解和理解邻里问题和民怨,应对该问题需要建立可靠的监控、搜集和评估传言的机制[11]。 内乱问题国家顾问委员会也建议警察机构建立情报机制,提供可靠信息,以应对城市暴动骚乱问题[12]。
为了推动这 些 建 议 的 落 实, 美 国 司 法 部 成 立 执 法 援 助 局(LEAA),基于“ 应对犯罪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情报数据“[13]的认知,为大量情报系统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14]医,执法情报工作获得快速发展。
1.2、20 世纪 70-80 年代:盛极而衰的执法情报工作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政府认识到对毒品的迷恋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15],组建禁毒署(DEA),成立“联合情报处“ (Unified Intelligence Division),建立国家禁毒情报系统共享禁毒情报信息[16],以应对毒品犯罪。
1974 年,美国司法部要求建立区域情报中心,负责搜集和传递有关毒品、非法移民和走私武器的信息,为全国的执法机构提供支持[17]。 随后埃尔帕索情报中心(El Paso Intelligence Center,简称EPIC)成立,成为美国最早的情报融合中心之一[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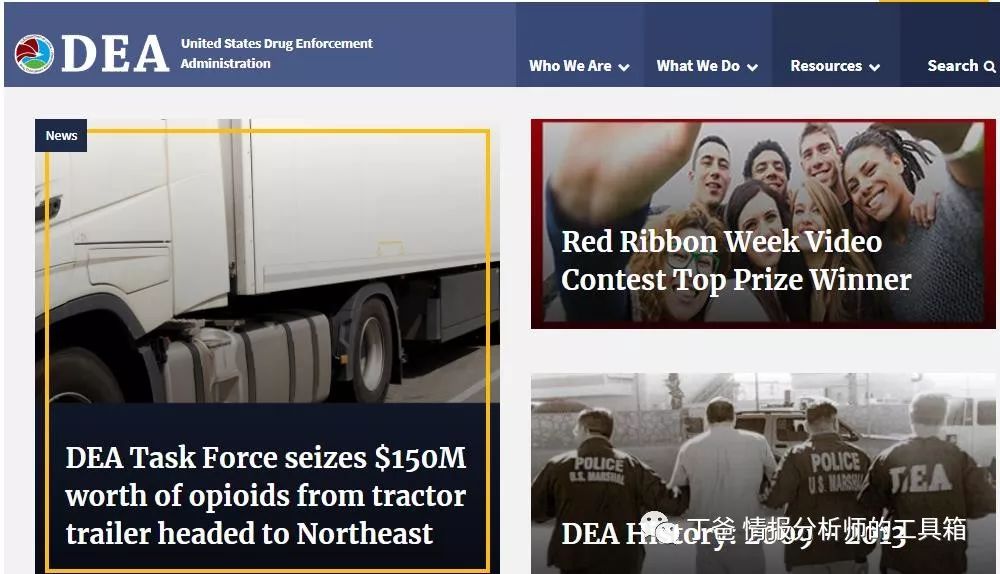
1973 年,美国国家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对情报工作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建议每个州都应该建立一个集中的情报搜集、分析、存储和传递系统,每个警察机构均应积极提供信息并从系统中获取情报,每个警察机构都应至少指派一名专人负责州情报系统的联络工作,以减少有组织犯罪和维护公共秩序[19]。
1974 年,美国司法部资助创建区域信息共享系统(Regional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简称RISS),1974-1981 年间先后创建 6 个RISS 中心,成为美国举足轻重的情报共享融合机制。
1976 年,美国国家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有组织犯罪工作组报告》、《 骚乱与恐怖主义工作组报告》 中集中阐释了系统的执法情报思想,建议建设“需要知道”和“有权知道“的情报文化,确立销毁情报记录的标准,建立情报工作个人和组织问责制,并要求各州应考虑与邻州之间加强犯罪信息共享进程,每个地方执法机构的情报部门应与各自州的情报体系保持一致,各州和地方情报部门都应为联邦机构提供支持,要为地方、州和区域情报体系建设建立可操作的政策和规程以确保效率与效益,每个机构都应指定专职官员负责向首长报告并监督情报业务,每个机构都应制定规程确保对信息进行适当的甄别和传递以确保安全[20]。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执法情报工作进入低潮期。
历经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蓬勃发展,执法情报工作成为公众广泛关注的议题,民权意识的觉醒以及执法情报的滥用,有关公民自由权利投诉、法律诉讼、合意判决频现[21]。
执法情报机构与政府部门迫于压力开始建立政策规范以规制犯罪情报工作,1976 年执法情报联盟(LEIU) 制定了犯罪情报部门文件指引,1980 年犯罪情报系统运行管理联邦规范(28CFR Part23)发布。 尽管如此,执法情报工作仍备受公众怀疑,许多执法机构开始弱化情报搜集与共享能力,甚至有的干脆撤销情报部门[5],美国执法情报工作进入低谷期。
1.3、20 世纪 90 年代:情报主导警务思潮的兴起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迎来新的警务革命浪潮,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掀起以情报共享与分析为核心的情报主导警务运动。 这一时期,问题导向警务、比较统计警务、情报主导警务等思想与改革运动勃兴。
问题导向警务基于“SARA”模型,强调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扫描(Scan)发现问题,通过分析(Analysis)理解问题,进而提出应对策略(Response),评估(Assessment) 其有效性[22],“扫描、分析、评估”的实质是情报工作。
比较统计警务思想源自美国纽约市警察局 90 年代的实践探索,纽约市警察局为了解决辖区治安混乱的局面,推行计算机统计(Comp Stat)计划,将警察管理和行动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精确打击和预防犯罪[23],取得巨大成功,被认为是情报主导警务(Intelligence-Led Policing,简称ILP) 的雏形。
此期间,禁毒和反恐领域的情报工作发展迅速,高危贩毒地区(HIDTA) 情报中心、烟酒/ 枪支和爆炸物管理局(ATF)地区枪支犯罪中心积极推动联邦、州和地区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改进信息交换与共享,专注于发展情报分析师的专业技术知识,为行动者提供情报支持[24-25];
中东地区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达雷斯萨达姆、坦桑尼亚、内罗毕、肯尼亚等国家地区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案,让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本土已成为恐怖分子的重要目标,提高预测、防范和应对恐怖袭击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能力,成为美国执法界、情报界的战略优先事项。
为应对新兴威胁,1999 年美国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应对能力顾问组“吉尔摩委员会(Gilmore Commission)强调:保护涉密国家安全信息及其来源与获取方法是必须的,但应该且必须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横向纵向信息共享,确保将信息及时提供给那些需要信息应对潜在威胁以有效保护家园的人[26]。
90 年代,美国开始大力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执法信息化建设随之快速发展,执法在线系统(LEO)、国家DNA 数据库与索引系统(CODIS)、指纹自动识别集成系统(IAFIS)、国家实时犯罪背景核查系统(NICS)等一大批执法信息系统平台建成使用,为执法情报共享融合与情报主导警务实践奠定了信息化基础。
2、“9·11“之后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的发展变革
“9·11”事件是美国执法情报工作的转折点,“9·11”委员会报告认为信息共享问题是未能防止 9·11 事件的关键因素[27],要求建立全国性的信息共享能力以提升发现、预防和阻止恐怖袭击的能力[28]。 此后,改善各级政府部门的情报搜集与信息共享能力成为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29]。
2.1、联邦各界情报共享融合建设
(1) 情报界。
2001 年,美国通过《爱国者法案》(PATRIOT),扩张情报机构的情报获取权。 《2004 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IRTPA) 全面推动国家情报体制改革,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建立集中的统筹协调与管理机制,具体举措有:设国家情报主任(DNI),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首脑和国家安全事务首席情报顾问,监督和指导国家情报计划的实施;设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ODNI),统筹协调联邦情报力量;先后成立恐怖分子威胁整合中心(TTIC)、恐怖分子筛查中心(TSC) 和国家反恐中心(NCTC),归口管理涉恐情报信息;

设专门负责情报整合的国家情报办公室副主任,创建情报界执委会、跨界分析产品委员会、情报界信息共享执委会等协调议事机构推动共享与整合[30]。2008 年出台《 情报界信息共享战略》对情报界的信息共享作出统一部署。
(2)国土安全界。
《2002 年国土安全法》授权成立国土安全部(DHS),负责推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以及私营机构之间共享信息,以提升侦测、发现、理解和评估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国土安全漏洞评估的能力[31]。
《2005 年国土安全部信息共享备忘录》在信息分析与基础设置保护局(IAIP) 的基础上建立情报与分析办公室(I&A),由负责信息分析的副部长兼任I&A 负责人,并作为国土安全部首席情报官(CINT)统筹协调国土安全情报工作。
2006 年DHS 成立国土安全情报委员会(HSIC),由主管情报与分析的副部长兼首席情报官担任主席,由I&A 部门的高级官员、关键情报官员(KIO) 以及首席情报官邀请的其他官员组成[32],作为顾问机构负责DHS 情报工作的监督管理、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绩效评估、预算建议、处理敏感信息共享争议等。
2007 年DHS 成立信息共享治理委员会。 《2007 年 9·11 委员会建议实施法》将DHS 的情报改革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授权I&A 负责“审查、分析并为信息共享治理政策与程序提供改进建议“,以解决“9·11“委员会强调的“联合情报工作的结构性障碍”,并将I&A 负责人提升为情报与分析次长(Under Secretary),兼任DHS 首席情报官。 2008 年《国土安全部信息共享战略》和 2013 年《国土安全部信息共享与防护战略》对国土安全信息共享作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3)执法界。
2003 年美国制定并发布《国家犯罪情报共享计划》(NCISP),要求所有执法机构均应采纳NCISP 提出的情报主导警务最低标准,从职责使命、管理与监督、人员选拔、培训、安全、隐私权利保护、情报产品的开发与传递以及责任机制等 28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为美国执法情报工作提供了改革蓝图[33]。
2004 年犯罪情报协调委员会(CICC) 成立,负责协调各级执法机构贯彻落实 NCISP,组织和参与了大量执法情报政策标准的开发,包括《执法分析标准》、《犯罪情报培训最低标准》、《执法分析师认证标准》、《国家犯罪情报共享计划 2.0》 等,为执法情报的规范化、标准化与制度化建设夯实了基础。
联邦调查局(FBI)作为情报界主要成员以及重要的执法机构,认识到建立综合情报部门以协调活动、整合资源的重要性,积极推进情报体制改革:
一是设立新部门“情报办公室”(OI)和新岗位“情报执行助理局长“(EAD-I),统筹FBI 情报工作;
二是在 56 个地方办公室设立地方情报工作组(FIGs)负责协调当地资源开展地方情报工作;
三是成立国家联合反恐工作组(NJTTFs),负责协调全国 84个联合反恐工作组(JTTFs)[34]。
2004 年司法部部长备忘录《进一步强化联邦调查局能力建设》 要求在OI的基础上建立情报处,该意见在《2004 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 中得到确认,2005 年FBI 情报处(DI)正式成立。
2014 年FBI 进一步强化情报集中管理,将情报处、局情报委员会、合作伙伴办公室、私营部门办公室等力量整合成情报分部(IB),由FBI 执行助理局长兼任 FBI 情报分部部长,统筹FBI 情报活动的监督管理以及外部合作[35]。FBI 还创设了信息共享政策委员会、首席信息共享官等机构或职位为信息共享提供支持。
2.2、州和地方融合中心建设
“9·11” 事件之前,州和地方执法情报工作缺乏全国范围的统筹规划,各级执法部门、国土安全部门依托内设情报机构以及行业内的情报协作“自给自足“,FBI 在全国各地的地方情报工作组(FIGs)、联合反恐工作组(JTTFs) 主要为FBI 的中心任务服务,RISS 中心尽管为地方执法机构服务,但难以架起地区之间、地区与联邦之间共享的桥梁。
“9·11”事件后,在各界呼吁推动共享的浪潮中,州和地方政府感受到蓬勃发展的国土安全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开始积极利用联邦资金建设属于本地的融合中心[36],以弥补国土安全、恐怖主义和执法信息共享方面的不足[37]。
2001 年美国诞生 2 个融合中心,2003年出现第一波融合中心建设高潮[38],这批早期的融合中心是州和地方政府自发创建,而非出自联邦的决策或授权[39],各个融合中心就像一个个独立的“烟囱“,相互之间无法交换信息,联邦尚未出台任何标准或指南用于解决融合中心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40]。
2005 年融合中心建设出现第二波高潮[37],联邦政府开始认识到融合中心的战略价值,着手支持和统筹推动全国融合中心网络建设。 国土安全咨询委员会(HSAC)建议“每个州都应建立一个一周 7 天 24 小时全天候运行的‘全源‘(all source)的和跨行业的‘信息中心’作为信息融合中心”[41]。
国土安全部与司法部等部门通力合作先后制定发布《情报信息共享计划:国土安全情报 &信息融合》、《融合中心指南》(1.0 版和修订版)等文件,围绕融合中心的任务目标、治理、协作、备忘录、数据资源、互联互通、隐私与公民自由、安全、物理设施、人力资源、培训教育、情报服务与产品、政策与程序、绩效评估、资金与传播计划等 18 个方面为全国融合中心建设提供统一指引[42]。
2006 年《信息共享环境实施计划》 明确要求将融合中心集成到国家信息共享框架中,建立全国性的融合中心集成网络[43]。
2007 年《国土安全州长指南》将情报融合中心作为州长工作的 10 个“关键要点“之一[44]。
《2007年 9·11 委员会建议实施法》以立法方式界定了融合中心的含义,确立了“国土安全部州、地区和区域融合中心计划”。
《国家信息共享战略》将融合中心定位为“州、地方环境中接收和分享恐怖主义信息、国土安全信 息 以 及 与 恐 怖 主 义 信 息 的 中 心 节 点 (focuspoints)“,将其列为国家优先事项,并进一步明确了融合中心的职责任务以及联邦、州、地区政府建设融合中心的职责分工[45]。
2008 年《州和主要城市地区融合中心的基准能力》 面世,随后《 融合中心技术指南》、《融合中心技术资源路线图》、《定义融合中心技术业务流程:一种规划工具》等指南性文件陆续诞生,为全国融合中心建设提供了统一的能力标准、技术框架和路线图。
2010 年,各融合中心主任和联邦政府共同研究确定了融合中心的 4 项关键业务能力(COCs) 和 4项必备能力(ECs),据此每年对融合中心网络整体能力进行年度评估,以评促建,至 2015 年国家融合中心网络步入成熟阶段[46]。
2014 年《2014-2017 全国融合中心网络国家战略》 出台,全面阐述了国家融合中心网络(NNFC) 建设的愿景、使命、基本目标、主要任务与实现路径,明确了 37 项行动计划[47]。 国家融合中心网络的建设与发展弥补了州和地方情报能力的不足,为应对“ 所有犯罪、所有威胁、所有风险” 建立了“跨行业、跨辖区、跨机构、跨领域“的信息共享与情报融合枢纽。
2.3、国家“信息共享环境” 建设
在情报界、国土安全界、执法领域改革的同时,联邦政府大力推进国家整体性的信息共享环境(Information Sharing Environment,简称ISE) 建设,为国土安全、情报、执法、国防、外交等 5 个领域提供更为广泛的情报支持。
2004 年美国第 13356 号总统行政令《加强反恐信息共享以保护美国人民》要求设计和使用信息系统时应把 “机构间的反恐情报交换“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并指示建立信息系统委员会以推动相关建议落实。
IRTPA 将信息共享环境(ISE)建设纳入法律框架,授权建立ISE,要求“以符合国家安全以及隐私与公民自由权利保护等现行法律标准的方式共享涉恐信息”,设ISE 项目主任(PM-ISE),负责ISE 规划、监督管理与实施,建立信息共享委员会(ISC),为总统和PM-ISE 提供支持。
2006 年,PM-ISE 按照 IRTPA 的要求,与有关部门合作研究制定了《信息共享环境实施计划》,为ISE 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与行动步骤,该计划要求每个州都必须确定一个融合中心作为联邦 ISE 和州、地方、部落执法机构(SLTLE) 之间信息共享的纽带。
此后,围绕ISE 建设,美国发布了总统备忘录《支持信息共享环境的需求和指南》 (2005 年)、《与信息共享环境有关的职能配置》(2007 年)、《ISE 事业结构体系框架》(2007年 1.0 版和 2008 年 2.0 版)、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备忘录《ISE 项目主任的职责》(2007 年)、《国家信息共享战略》(2007 年)、《 促进涉密网络安全和责任共享以及保护涉密信息的结构改革》 (2011 年第 13587 号总统行政令)、《国家信息共享和安全战略》(2012 年)等系列政策标准,为全面推进国家安全信息共享环境建设提供了指引。
3、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发展的特点
纵览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历程,呈现以下总体特征:
一是执法情报中心任务随着安全威胁因素的变化不断改变,早期以有组织犯罪、城市骚乱、毒品犯罪情报为中心,90 年代尤其“9·11“事件后反恐成为首要任务,如今转向“所有威胁、所有犯罪”;
二是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不断变迁,从早期以协会为主要交流方式的 LEIU,到基于信息系统的RISS,再到以联邦执法在线(LEO)为代表的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充分体现了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的技术依赖性;
三是执法情报理念不断演变,从早期自发建立信息交换组织,到联邦政府自觉推动情报信息共享融合,再到以“情报主导”为指导思想推动跨层级、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跨界“大融合,情报融合理念不断更新换代。
具体说来,各阶段特征如下:
(1)20 世纪 50-60 年代:
美国执法界开始认识到应对犯罪的主要问题是缺情报数据,联邦决策咨询机构开始敦促执法机构建立情报部门,呼吁联邦加大资金与技术支持力度,推动地方执法情报工作的发展。这一时期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一是执法情报任务侧重于应对社会骚乱和有组织犯罪问题;
二是联邦层面没有出台指导各地情报共享融合的政策、指南或战略规划,各地执法机构基于自身需求自发开展情报信息交换与协作活动,LEIU 信息共交换机制是典型代表;
三是 60 年代后执法情报共享问题开始进入政府决策议程,联邦开始自觉推动情报信息共享。
(2)20 世纪 70-80 年代:
美国执法情报工作历经了“盛极而衰”的发展过程。 70 年代初,执法情报工作蓬勃发展,以RISS 为代表的信息共享系统建设大大促进了各地执法情报工作,其特点与突破主要有:
一是参与的广泛性,要求所有警察机构都建立情报能力;
二是应对问题的多元化,任务重点扩展到为打击非法贩卖毒品、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暴力犯罪、贩卖人口、身份盗窃、恐怖活动等诸多领域;
三是创建了区域信息共享中心(RISS) 机制,并将与公众、私营机构进行信息共享纳入共享框架;
四是重视情报文化的建设,要求培育“需要知道”和“有权知道“的情报文化。 然而,随着执法情报信息搜集和共享能力不断增强,针对执法情报部门侵权的诉讼不断增多,美国开始制定规制犯罪情报工作、保护公民隐私的政策,国会通过“只有在合理怀疑该人涉及犯罪行为或活动,且这些信息与犯罪有关,方可搜集、保存有关个人的犯罪情报信息”的限制条 款, “ 犯 罪 情 报 系 统 运 行 政 策“ ( 28CFR Part23)[48]正式颁布等,许多执法机构开始削减情报投入,执法情报工作发展势头从高潮跌入低谷。
(3)20 世纪 90 年代:
执法情报工作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一是发源于英国的情报主导警务理念在美国萌芽,纽约市警察局推行Compstat 警务模式,强调数据驱动,以犯罪数据分析为中心,为提前预警、精确打击、科学决策与目标防范提供决策支持,为各地执法情报工作提供了成功样本。
二是在工作重点与任务方面,除了应对传统的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城市骚乱等犯罪现象之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执法情报工作的重点领域。
三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为执法情报工作的信息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期间执法界开始大力开发各类信息系统平台,并推进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
(4)“9·11”事件之后:
美国政府启动“二战“以来最重大的情报体制改革[49],执法与国土安全情报工作呈现诸多新特点:
一是以反恐为优先任务推动情报工作跨层级、跨领域、跨行业、跨辖区的“ 跨界“ 共享融合。 联邦层面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国家信息共享环境(ISE),为情报、执法、国土安全、国防、外交事务五大领域提供情报支持;州和地区层面以融合中心建设为基石,建立面向“所有犯罪、所有威胁” 的国家融合中心网络,整合执法、消防、应急、边防、医疗卫生、网络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多领域的涉恐与犯罪信息,并作为联邦、州、地方政府信息共享的中心节点,架起联邦和地方协作的桥梁。
二是建立集中的情报管理体制,情报界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信息共享环境建设设立 PM-ISE 和 PM-ISE 办公室,国土安全部设首席情报官并兼任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和 I&A 办公事主任,联邦调查局整合情报处、情报委员会等力量成立情报分部,这些改革举措均贯穿着同一个中心思想,即建立集中的管理体制以整合资源。
三是更加重视州和地方政府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将联邦、州、地方、部落和区域(FSLTT)以及私营部门视为利益相关方纳入国家信息共享框架,把地方融合中心作为横向、纵向信息共享的枢纽。
4、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的关键成功因素
综上,美国推进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的关键成功因素集中体现在:以“情报主导“为指导思想,以“共享融合”为逻辑主线,以情报机构重组、系统互联互通和情报分析能力建设为重点,以隐私权、知情权保障与互利互惠为基石争取广泛信任与支持,培育“信息管家“与“需要分享”的情报文化破除共享壁垒,通过灵活的机制建设与制度设计,推动跨层级、跨部门、跨辖区、跨行业的“跨界融合“,以应对“所有犯罪”和“所有威胁“。

4.1、情报主导:执法情报工作发展变革的指导思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情报主导警务(Intelligence-LedPolicing,简称ILP)理念开始兴起。 美国纽约警察局实施以数据分析驱动科学决策、迅速行动和精准打击的Compstat 警务模式,取得巨大成功,被认为是ILP 模式的雏形。
“9·11” 事件之后美国发布改革蓝图《 国家犯罪情报共享计划》,明确要求所有执法机构均采纳情报主导警务最低标准。
情报主导警务是一种管理理念、协作哲学、业务模式,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强调把情报工作置于基础性、先导性位置,将情报视为影响执法决策过程与战术行动的关键性乃至决定性因素;作为一种协作哲学,强调广泛汇集多源信息以理解工作环境[50];
作为一种业务模式,强调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广泛地收集违法犯罪与恐怖威胁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综合研判,准确把握威胁态势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全方位地指引决策,优化资源配置,精确打击防范,以有效控制威胁与风险。 美国执法情报发展改革历程正是这种理念、哲学、模式的实践探索与应用过程。
为了灌输“情报主导“的理念,制定《犯罪情报培训最低标准》,将培训对象分为执法官员、执法人员、情报官、情报分析师、一般情报工作人员以及培训讲师等 6 类,设定情报培训最低标准,要求全员接受符合最低标准的情报培训,培训的首要目标就是让执法者了解/ 理解情报主导警务以及犯罪情报共享计划。 这些实践反过来丰富了情报主导警务的思想内涵,进而重塑美国执法情报业界文化与生态,形成良性循环。
4.2、共享融合:执法情报工作发展变革的逻辑主线
美国上世纪 50 年代建立执法情报联盟(LEIU),60年代建立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70 年代建立区域信息共享系统(RISS),90 年代建立以执法在线系统(LEO)为代表的各类信息系统与平台,都是“共享融合”理念的产物。
“9·11“事件后美国执法情报“共享融合”理念与实践发展到全新的高度,“共享融合“成为整个情报体制改革的初衷与内核:联邦层面,情报界、国土安全界、执法界各自积极推进本行业资源整合,建立更为集中的管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建设跨界的信息共享环境(ISE);
地方层面,积极推动融合中心网络建设,将其纳入整个国家信息共享框架,构建起全国范围的“纵向、横向、 共享的“超级信息共享系统;同时,强化情报“分析” 能力建设,促进信息向情报转化,建立“ 跨界( 情报、执法、国土安全、国防、外交、私营机构)、跨行业/ 领域( 刑事犯罪、消防、应急、医疗卫生、边防、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安全等)、跨层级( 联邦、州、地方、部落等)、跨辖区“的以“接收、分析、收集、传递” (COCs) 为核心业务能力的“超级国家情报分析与服务系统“。
概言之,“共享融合”是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推动执法情报改革的逻辑主线,正如 2007 年《国家信息共享战略》所指出的,情报信息共享框架曾经让美国赢得冷战,现在需要更加机动灵活而具有弹性共享机制,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威胁。 而情报融合中心的诞生,被认为是“至少在过去的 25 年犯罪情报格局中最重要的变革“[51]。
我国自金盾工程开建至今,执法信息化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共享融合” 的信息壁垒、技术壁垒、利益壁垒、文化壁垒等仍然突出,共享融合范围和深度有限,有关部门可借鉴美国做法,推动建立跨层级、跨地区、跨行业的情报融合中心,突破传统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相关行业之间的壁垒,实现更为广泛的共享与深度融合。
4.3、情报分析:情报融合进程中的核心能力
多元信息的共享汇集,是零散、残缺、低价值密度的原始数据,通过科学的分析研判,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情报产品,及时传递给合适的用户,是情报融合的关键。
美国认为,情报主导警实际上是分析师驱动警务(analyst-directed policing),因为情报是分析师的产品[52]。 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特别重视情报分析队伍培养和情报分析方法技术工具的研发。
早在 1984 年美国有组织犯罪总统委员会在一份审查报告中便着重指出,有效的情报分析是执法机构成功处置复杂犯罪的关键工具[53]。
《犯罪情报共享:一项推动地区、州、联邦层面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国家计划》明确指出美国执法界与情报界“ 面临泛滥的‘ 信息‘但却缺乏简明的、有针对性的、经过评估的‘情报’“[54],鉴此,《国家犯罪情报共享计划》 要求开发情报分析标准,并为全国执法机构推荐分析工具与分析产品,确保情报及时、可靠、精准。
此后有关情报分析培训最低标准( 含初级、中级、高级)、情报分析流程标准、情报分析产品标准、情报分析师能力标准、分析师认证标准、情报职业发展路线图等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 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9·11 委员会建议实施法》等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情报分析能力建设的要求和拨款授权。
根据FBI2015 -2018 年的预算报告,FBI 各财政年度获批职位总数维持在 3.5 万左右,其中情报分析师岗位约 3300 名左右,占比 9.3%-9.6% [55];
美国禁毒署(DEA) 岗位职数为 8000 余人,其中情报分析师 900 人左右,历年占比均在 11% 以上[56];
2016 年财政年度美国情报融合中心工作人员职数为 2539 人,其中分析人员 1051 人,占比高达 41.4% [57]。
可见美国对情报分析的重视程度,我国较之,在情报分析队伍建设、情报分析知识管理理念以及投入方面相对落后,亟待加强。
4.4、体制调整:随势按需灵活调整的改革机制
官僚体制有其内在的惯性和惰性,美国执法情报工作发展变革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9·11” 委员会报告针对情报体系改革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在过去 40 年的报告中都出现过,然而,直到“9·11“事件之后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58]。
“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改革打破了这种“僵化“格局,紧跟威胁环境的变化及时、灵活进行体制机制的调整以有效应对威胁。
管理体制方面,通过已有机构调整、新机构创设以及建立工作组、任务组、焦点小组、委员会等方式灵活整合相关力量和资源,围绕特定任务、项目、计划,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例如联邦调查局“9·11”之后情报办公室、情报委员会、情报处、情报分部的机构创设和调整,国家恐怖威胁整合中心、国家反恐中心的职能调整和机构设置,国土安全部、信息分析与基础设施保护局、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国土安全情报委员会、首席情报官的设置,信息系统委员会、信息共享委员会、信息共享环境项目主任办公室、犯罪情报协调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类机构内部和跨机构协调的技术、标准、政策委员会等机构的创设,均充分反映了美国情报共享融合工作“随势按需而变“的灵活特点。
执法情报的中心任务方面,也因时而动,随势而变,过去“以反恐为中心”,现在转向应对“所有犯罪、所有威胁、所有风险“,过去强调行业内的信息共享融合,当前突破传统边界推行“跨界融合”等。
我国政府机关在机构设置、机构改革、管理体制等方面制约因素甚多,稳定有余而灵活不足,可考虑借鉴美国做法,针对重大议题、重大决策以及各类优先事项,以顾问委员会、工作组等方式组建临时性任务团队攻坚克难,在坚持政策标准延续性的基础上为灵活性提供足够的空间。
4.5、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发展路径
统一标准是共享、融合与协作的基本前提,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是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美国执法情报界特别重视顶层规划和制度设计,犯罪情报协调委员会指出,只有所有机构,不管规模与司法管辖权力大小,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有效和高效地开发和分享情报,从而建立更为安全的国度[36]。
“9·11“之后,《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法》、《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9 ·11 委员会建议实施法》、《国家犯罪情报共享计划》、《 信息共享环境实施计划》、《国家信息共享战略》、《 融合中心指南》、《犯罪情报培训最低标准》、《执法分析标准》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指南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不断诞生,并通过逐层细化、逐项分解的方式具化落实,通过成熟的评估机制、外部的监督机制以及最佳实践推广机制促进优化,最终实现“自上而下有规范”、 “自下而上有活力“、“ 全国发展有方向”、“ 具体运行有指引 ( 路径)冶,规避“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
我国执法部门近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实战部门基于现实的任务压力和业务需求驱动,呈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但顶层设计规划滞后于实践发展,各地自行其是,系统标准不一,工作模式千差万别,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程度不高,精细化不足,重复建设严重,信息共享融合困难,难以形成合力。 进一步加强和优化顶层设计,为全国范围的情报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统一规范、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标准、规范和指引,是我国当前执法情报工作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4.6、权益保障:争取最广泛的信任与支持
美国在推动执法情报共享融合过程中非常重视三类权益的保障,为共享融合提供了强大的动因:
一是公民隐私与自由权利(P/ CRCL) 保护,美国吸取 20 世纪 60 年代至70 年代针对执法情报部门的诉讼浪潮的教训,重视P/CRCL,几乎所有有关情报工作的法律政策、标准规范、规划指南,均会就隐私与公民自由权利保护提出要求或限制条款,并在信息系统开发、开放使用、安全许可等方面采取措施以保护公民隐私。
二是保障知情权,《国家犯罪情报共享计划》 第 14 条建议明确要求提升政策透明度,在不影响安全与工作的前提下应向公众公开犯罪情报工作政策,以培育执法机构、决策者及其服务的社区之间的信任关系。
三是合作伙伴之间的利益保障,维持信息共享融合与紧密协作关系的基石是“风险共担” 和“利益共享“,仅仅依靠传统的法律授权、行政命令等对信息共享责任进行强制规定缺乏足够的内驱力,难以激活利益相关方搜集与分享信息的热情和创造力,建立情报信息双向流转、地位对等、互惠互利机制,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共享协作的意愿与积极性。
我国执法部门应借鉴美国做法,建立健全隐私保护政策与规范,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适度采取开放政策,消除情报工作的神秘感,接受外部监督,改变传统的依靠法律政策和行政命令强制要求索取信息的方式以及“等、靠、要”的理念,以“互惠互利“、“信息双向流动”为指导思想积极推动情报搜集、查询、使用、传递、授权机制改革,以赢得更广泛的公众信任和广大一线用户的合作与支持。
4.7、文化转变:培育“信息管家“与“有责任提供”的共享文化
情报信息共享融合面临技术标准、安全保密、权利分割、利益壁垒、信任关系等诸多障碍。 美国执法界致力于培育良性情报文化以缓解这些问题:
一是改变过去“原创者掌控“ (originator controlled) 的“所有权” (ownership) 文化,培育“ 信息管家“ (information stewards)文化[59],即情报部门并非情报信息的“所有权人”而是“信息管家“,这种改变使情报信息作为 “我的资源”变成了代管“大家的资源“,彻底改变了“情报用户”和“情报工作人员“的角色与关系,大大削减了共享的阻力;
二是改变传统的“ 需要知道”(need to know)的文化,培育“有责任提供“(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或“ 需要分享” (need to share) 的文化[60],变“索取“为主动“分享”。并将这种理念贯穿于情报人才招募、培训、考核等各环节;
三是确立“ 共享是原则而不是例外“[45]的共享文化,通过合理的定密机制以及信息获取许可方式,避免因过度保密阻碍共享,确保有权知道且有必要知道的人能够及时获取相关情报信息。
情报文化作为情报工作理念、价值观、信念、精神等的集合,是情报工作的灵魂和不竭动力,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信息管家”、“需要分享“、“有责任提供”、“共享是原则而不是例外“的情报文化,将为执法情报工作广泛共享与深度融合提供文化动能。
本文参考了项目组成员王晨颖、曹君、李修丞、刘楠、梁乐萌、张静、黄一洋等翻译的部分政策文本,在此表示感谢。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公众号ID:dingba2016)
声明:本文来自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
